核酸与返乡,一张纸上的乡愁与归途
1
2026-01-08
凌晨四点,县城汽车站的候车厅里,长椅上的男人突然惊醒,他下意识去摸口袋,触到那张对折的硬纸片时,呼吸才平缓下来,纸片边缘已经磨损,上面的黑色字体依然清晰:“核酸检测阴性”,他把证明贴在心口,像护身符,窗外,第一班开往深山的巴士正在发动,车头灯刺破浓雾。
这条返乡路,他走了二十年,起初是绿皮火车哐当哐当三十小时,后来是高速公路七小时,是七十二小时内的核酸报告,母亲在电话里说:“村里要看的,没有那个绿码,进不了祠堂。”他不知道祠堂和绿码何时建立了同盟,只知道这张纸片成了新的通行证——比身份证更紧要,比车票更沉重。
车在山路上盘旋,邻座的女人一直握着手机,屏幕上是她两岁儿子的照片,她已经十三个月没见到他了。“上次回去,他躲在外婆身后叫我阿姨。”她苦笑着,给我看相册里的截图:一个皱巴巴的二维码,下面小字标注“某医院核酸检测预约”。“抢了三天才抢到,比春运票还难。”她说,声音被发动机轰鸣吞没一半。

这些证明正在重塑“故乡”的定义,村口曾经的槐树下,现在立着临时板房,穿防护服的人手持体温枪,外出务工者不再是“从广东回来的”“从上海回来的”,而是“持48小时核酸回来的”“需要居家监测的”。 kinship被重新分类,依据不再是血缘亲疏,而是风险等级,一位老人告诉我,他孙子大学毕业回家工作,“不是因为想家,是因为怕突然封控回不来家。”当返乡变成需要精密计算概率的事件,“家”的概念也在摇晃。
更深的变化发生在时间里,传统节日的团聚被“防控窗口期”取代,清明祭祖,家族群里最先讨论的不是纸钱香烛,而是各地防疫政策对比图,中秋团圆,月亮通过手机屏幕共享,月饼快递需要附上消毒证明,时间被切割成“核酸有效”与“核酸失效”的片段,返乡不再是心血来潮的奔赴,而是需要规划的项目管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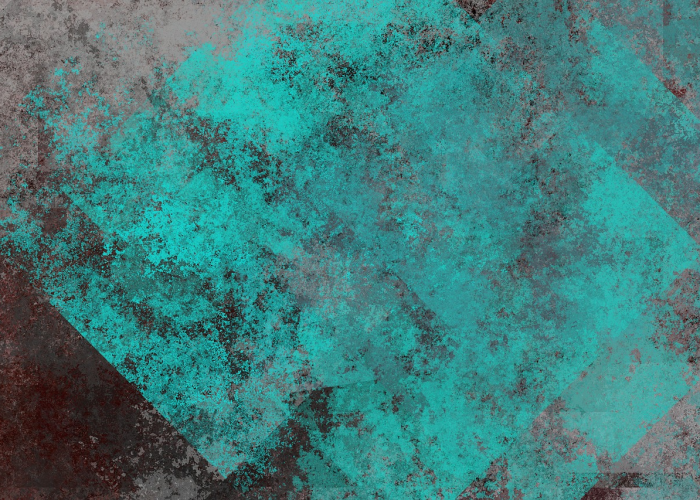
在所有这些规训与计算之下,一些更古老的东西在流动,我遇到一位徒步穿越三个省边界的男人,背包里除了干粮,就是层层包裹的核酸试管。“没办法,老父亲病重。”他穿越农田、山林,有时甚至需要夜间行走,就为了避开检查站,那张已经过期的核酸报告被他保存着,“至少证明我这一路是安全的。”他说,这种近乎悲壮的返乡,揭示了一个悖论:我们越是试图用科学手段确保安全,越凸显出人类情感的不可控与不可测。
车到终点时,雾散了,村口的检查站前,人们默默排队,手机屏幕的蓝光映亮疲惫的脸,轮到我了,工作人员扫了我的健康码,又仔细核对了核酸报告日期,—他抬起头,用方言说:“是老三家的孩子吧?长这么大了,快进去,你奶奶从早上就在村口转悠了。”
那一刻,所有码、所有证明、所有隔离与监测筑起的高墙,突然裂开一道缝,透过这道缝,我看见“核酸”与“返乡”这两个词在晨光中颤抖、融合,它们共同构成这个时代的隐喻: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精确地知道自己的身体,却比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能否抵达想去的远方;我们被数据编织的网紧紧包裹,但网眼之间,仍有月光漏下,照亮人类最古老、最顽固的乡愁。
巴士发动,载着下一批返乡人,他们口袋里,崭新的核酸报告正在生成,而群山深处的村庄,炊烟照常升起,像在天空写着什么无法被转码的、古老的消息。
发表评论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